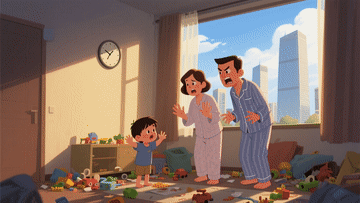石匠周志华坐在长石板上,看着满天的蓝。
西井峪村刚下了场雨,整个村子的石头被雨水和阳光洗刷得水亮光滑。绿色的青苔铺垫在大地缝隙,夏蝉如雷。
这里是周家世代居住的三合院,院子周围是石头墙,村子周围群山连绵不绝。
周志华皮肤黝黑,身形干瘦,短发,脸上皱纹纵横,眼袋硕大,一双眸子黑得精亮。他是天津市蓟州区“石头垒砌技艺”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,从18岁开始砌石,到今年已有37个年头。
“算起来,我是第三代了,带我的老师傅现在86岁了。师傅不能手把手教你,只能点拨,好比这块石头不规整,告诉你‘这块石头垒得不中啊’。功夫得靠自己磨,自己练。”一开口,周志华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,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从那瘦削的身体里迸发出来。
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西井峪村是有名的“石头村”,整个村子就像石头的森林。周志华和石头打交道多年,熟悉锤子、凿子、钢钎、楔子、錾子,熟悉石头的脉络,他只用眼睛,就能丈量石头的大小。
周志华说,他垒的石头比别人的活要细。虽然村子里用的石头本身是平整的,但垒得越平才能越好看,这是细活。垒得一高一低的,那是糙活。
“细活还是糙活,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周志华摸着自己砌的石墙,果然是厚实古朴,清亮通透。
细活需要好眼,“眼珠必须得好使,不好使就麻烦了。”周志华指着自己那双又细又深的眼睛,“好比垒石头墙,需要10公分的石头,你打眼一瞅,这块就是10公分,不用拿尺子去量。”
看见路边有块平整的石头板,周志华跺了跺脚,笑着说,这就是村里的石头,好使。
西井峪村最高的石头墙有近6米高,100年不倒。村子里还有许多100年以上的老房子。在唐山大地震中,它们坚挺屹立,安然无恙。砌石手艺的纯熟高超,由此可见一斑。

西井峪村里一栋老房子。新华社记者曾晋 摄
正午过后,阳光猛烈起来。坐在石头上,周志华把黑色长裤脚挽了起来,露出伤痕累累的细瘦脚踝和小腿,触目惊心:密密麻麻的伤疤,少说也有上百个,层层叠叠的伤疤纵横交错,旧痕未愈又添新伤,就像镌刻在粗砺石头上的棱角斑纹。
用石头砌筑房屋,是一项充满困难并且极具技术性的手艺,而作为建筑材料的石头,也来之不易。在山上取材艰巨且危险。过去,开采时在采石场拿炮崩,再用梭子扎,将石头敲击成需要的大小,用车拉到现场后,这才进入砌石头的阶段。
周志华只读过一个月的初中,便到山里开山采石。在采石场干了3年之后,他拜师学石头垒砌技艺,先跟在师傅身边打杂,当小工,找原料,搬石头。在施工过程中,师傅一边干活一边教他怎样选石头,根据石头的颜色和形状,来区分这块石头的用途和摆放位置。之后的两年里,他开始和师傅学敲石头,给石头塑形使之达到理想的形状。师傅会根据石头的颜色和大小来教他手腕的发力技巧。
长年累月下来,石头磨着皮肤,硌着骨头,周志华梦里都知道石头的形状、大小、边角,墙路的宽窄装在了眼里,刻在了心里。
“皮肤都坏了。”他淡淡地说,那时候有小伙子跟在后边干活,用30多斤的大黄锤,噔噔就把脚趾头打折了。
“伤了的时候有休息一下吗?”我问。
“没有。”他没有一丝犹豫地回答。
他的手指,每根手指关节都弯曲着,指尖肉鼓胀起来,指甲经受多次砸伤,已然变形。我不忍再看,眼睛湿润。对他来说,砸手、砸脚,是很正常的事情,他的皮肤、他的身体已经像石头一样坚不可摧。
蝉鸣声越来越盛,在山里回响。周志华从屋子里拿出两个青绿色的梨,递给我。一口咬下去,酸而不涩,清凉的汁水很快在舌底下铺染开来。
周志华边吃边说,那时候苦,没东西吃,有些活急,也需要时间,两天两夜除了吃饭睡觉,就得不停干活。干完活他摘梨、柿子、樱桃、杏子吃,还去找掉下来的核桃和栗子,有滋味,好吃得很。
周志华叹了口气说,垒石头的这活累人,也挑人,需要好眼睛,好耐力。心灵手巧的人一点就通,但有些人一辈子也做不出细活。现在他还有个习惯,在山里,见到好看的石头就拿四轮车拉回来,就这样攒了很多石头。“好的石头要慢慢打磨,否则打疵了,就给糟践了。”
末了,他望着树荫说,“也好,现在生活好了,不需要那么累人,去干这活了。”

周志华望着庭院里的树。新华社记者曾晋 摄
我走出院子,周志华跟在身后,锁上门。他轻快地踱着步子,回到路边,身后的小路上都是一代代垒石头的人砌筑的房屋墙体,那些耗费了无数巧劲、腕力、心血的石头作品,那些看似粗糙随意但坚固无比的屋子,它们大小搭配、正斜相倚、薄厚互补、结实朴素。
“这些石头,棒着呢!”周志华说。(曾晋)